文 / 彭小华
抑郁症作为一个精神医学概念,在上世纪 80 年代从西方传入中国。近几十年间,特别是近 10 来年。按照社会学者肖易忻的说法,经过药企、学界、政府、媒体的广泛宣传、传播和教育,抑郁症在我国完成了概念的构建,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认知,患者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多。
《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表明,我国的抑郁症患者人数达到 9500 万。这意味着在每 14 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是抑郁症患者。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 - 2020)》显示,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 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 7.4%。
数据很庞大,比例也很大。即便如此,专家依然指出还未做到充分检出。这意味着实际患者的数量比目前检测出的要更多。
有了抑郁症这个概念之后,从青少年学生到官员,媒体所公布的自杀原因常常为“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会引发自杀行为,所以抑郁症显得很恐怖,这也就引起了社会、家庭、学校以及政府普遍的担忧和广泛的关切。从国家教育部开始,各省、市教育部门以及各个学校陆续制定政策,采取应对举措。
然而,从诊断方面来看,抑郁症的生理—精神医学模式不可靠;从致病原因方面来看,该模式也不可靠;从治疗方面来看,此模式同样不可靠。在西方,这个模式已经受到许多精神病学者和心理学者的批评。而在我国,这个概念和认识模式处于主导地位,并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个现象让人感到担忧。
抑郁是情绪症状,不是疾病本身
这些年,我接待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泰国、韩国等国的数以百计的抑郁症患者。有儿童、青少年,也有中老年、耄耋老人;有小学生、中学生,还有大学生、硕博士研究生;有全职妈妈、普通职员、中层管理者,也有专业人士、官员、企业家;有国内同胞,还有留学生、海外侨胞、二代华裔和白人……他们因抑郁症而寻求帮助,一旦被问及抑郁的原因以及发生和发展过程,都能说得明明白白。
当然,每个人抑郁的具体原因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面临的困难比较单一,有的人面临的困难则比较复杂且多元。但总体而言,都遭遇了可统称为人生困难或负性生活事件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人际冲突,像亲子、夫妻、婆媳等家庭关系方面的冲突,同学或师生关系方面的冲突,同事、上下级关系方面的冲突;还有失败或挫折,涵盖学业、职业、事业上的失败或挫折;以及意义感缺失、迷茫,还有疾病、生死忧惧等。其中,人际冲突或伤害是致使抑郁的主要缘由。其他方面的缘由,大多是合并了人际关系问题,或者是缺乏良好的人际支持。
《2022 国民抑郁症蓝皮书》表明,学生抑郁的缘由,77.39%是人际关系方面的,69.57%是家庭关系方面的。其他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大致上是相同的。
国际上的几十项抑郁症研究结论较为相近。比如,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有 75%的抑郁症是由“羞辱或困顿”这类事件所导致的,20%是由损失/丧失所引发的,5%是由危险事件所造成的。而所谓的“羞辱或困顿性”事件,实际上就是人际伤害的另一种表述。
美国精神病学家巴塞尔·范德考克是《身体从未忘记》的作者。他表示,超过一半的患者在童年时期经历过殴打、被抛弃、被忽视,甚至遭遇性侵,还有一些患者目睹过家庭暴力。他进而指出,遭受虐待和忽视的儿童是精神/心理障碍的主要人群。
然而,现在有一个被广泛传播的说法,那就是抑郁症的诱因并不清楚。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所谓的不清楚,实际上是从生理 - 精神医学的角度来说的,而从人文 - 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则是很清楚的。
抑郁症的诱因包括关系冲突/伤害、人生挑战或负性生活事件。当个体遭遇这些困难时,会产生一种消极情绪和行为反应,其核心表现为悲观、绝望、无助,觉得问题无法解决,没有出路。
进化精神病学的奠基人、《坏情绪的好理由》的作者兰多夫·内塞表明,抑郁属于情绪方面的症状,并非疾病本身,如同发烧、咳嗽是症状而非疾病本身那般。生理 - 精神病学在对抑郁症的认知上,犯了“把症状当作疾病”(VSAD)这一错误。范德考克也指出,抑郁症是关系方面的问题以及适应方面的问题,并非生理疾病。
被药物塑造的抑郁症社会认知
上世纪 50 年代起,美国开展了一场抑郁症药物治疗革命。其基本理论假设为,抑郁症是因患者大脑缺少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两种神经递质而引发的。然而,正如内塞所言,历经大半个世纪,耗费了大量金钱以及无数聪明人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这个假设仍未得到证实。
有一个事实最能说明问题,那就是抑郁症与其他生理疾病不同,到目前为止,它无法通过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的方式来诊断,而只能借助各种量表进行诊断。
在美国,抑郁症的诊断依据是美国精神病学会编纂的 DSM 诊疗手册,如今该手册已经发布了最新的第五版。在我国,使用的是 CCMD 和 ICD,这些诊断标准与 DSM 在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方面是相通的。
然而,抑郁症诊断手册在精神医学界也遭遇了诸多非议。范德考克觉得,DSM - 5 完全退回到了 19 世纪早期医学的那种做法。我们知晓它所发现的许多问题的根源,即便如此,它的诊断描述只是关注表面现象,却完全将潜在原因给忽视了。
范德考克所提及的“许多问题的根源”以及“潜在原因”,指的是患者所遭遇的人生方面的挑战和困难,“表面现象”则为抑郁情绪。他明确表示该手册“缺少科学性,诊断不可靠”,并且对病情的理解主要是由医者的心态所决定的,而非可验证的客观事实。
诊断结论除了具有主观、随意的特点外,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诊断标签会伴随人们一生,会对他们的自我定义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会让别人对他们另眼相看。
生理 - 精神医学认为,抑郁症无法被治愈,并且不以治愈作为目的,还会复发,所以患者需要终生服药。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把患者判处了终生监禁,让他们永远无法摆脱困境。
2021 年 11 月,我国教育部打算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这意味着会把被评估为有心理障碍的青少年学生贴上标签。这个比例被认为接近 25%。可以想象,如果真这样做,就表示至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升学、求职、升迁以及婚恋等方面,都会受到不利影响。他们的命运会因一个不严谨的精神医学诊断而变得更加艰难。
学生心理健康档案的事后来没了下文,但愿已经作罢了。
范德考克指出,在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精神药物成为了文化的重要支撑部分。然而,其效果并不理想。“倘若抗抑郁药真如人们所认为的那般有效,那么我们社会中的抑郁症本不应成为一个大问题。但实际上,抗抑郁药的使用量在不断上升,却并未使得抑郁症住院的数量减少。”
事实是,在过去的 20 年当中,美国接受抑郁症治疗的人数增多了 3 倍。每 10 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人在服用抗抑郁药。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儿童数量超过了 50 万。过度诊断以及药物滥用,已经成为了被广泛诟病的现象。
我国的情况如何呢?抑郁症的检出数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态势,在用药方面以及住院数量上也是如此。然而,患者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将更多的人纳入其中,从客观角度来看,这扩大了药品市场。
很多人知晓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存在生理性的副作用。然而鲜有人知的是,它们所带来的精神、心理后果更为严重。
药物对儿童成长的危害着实令人痛心。范德考克指出,药物能让孩子们更便于管理,使其攻击性降低,但同时干扰了儿童的动力、玩耍嬉戏以及好奇心,而这些对于儿童成长为功能健全且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服用这些药物的儿童还存在过度肥胖和患糖尿病的风险。
内塞指出,有经验的医生不会直接给发烧患者开具退烧药。他们会先确定导致发烧的原因并进行处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掩盖病因,从而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而抑郁症的药物治疗方式,不问病因,只处理情绪症状,这种做法就如同医生不管发烧的原因,直接给患者吃退烧药一样。这是违背常识的。
范德考克指出,药物能带来很大利润。主要医学刊物在发表关于精神健康问题的研究时,很少涉及非药物治疗的内容。探索治疗方法的那些实践者,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被称作“替代疗法”。希望我国能够避免和纠正这样的情况。
如何破除抑郁症医学化
药物被广泛使用会带来另一个后果,那就是转移了人们对潜在问题的关注,这些潜在问题指的就是人生的困难和挑战。大脑疾病模式使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权,把自己的问题交给了医生和药物。
范德考克指出,药物只是让感受变得迟钝了,它对解除感受没有帮助,也不能把感受从有毒的东西转变为盟友。
“有毒的东西”所指的是人生之中的困难以及挑战,这些东西会让人感到痛苦,具备“毒性”。然而,它们也能够成为人成长的契机,成为人的盟友。就如同哲学家尼采所讲的那样,“凡是无法将你杀死的,都将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而佛家则觉得,挫折是进行修行的良好时机,也就是如同王阳明所说的“在事情上进行磨炼”。
范德考克批评他的同行不关心患者的成就与理想,不关心他们在乎和爱的人以及恨的人,不关心他们的动力来源以及感兴趣的事物,也不关心他们的困难之处以及能带给内心安宁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关心患者生活和生命所处的那种环境,这样的治疗无法触及导致患者精神/心理痛苦的真实难题。
我参加过一次抑郁症专题活动。有一位分享嘉宾来自一家很著名的精神卫生医院。她讲自己平均看一个患者需要四分多钟。这么短的时间,仅仅能够来得及开药,没办法进行有意义的交谈,也没办法了解患者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以及为什么会抑郁,而只能给出开药这样一个“一概而论”的治疗方案。
有一类来访人群,他们不是以抑郁症为由来求助,而是以人生困难、挑战为由来求助。他们同样在经历着情绪的痛苦,也会感到焦虑、抑郁。然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抑郁症病人,他们所寻求的是解决困难的办法,而非去看病、吃药。
处理抑郁的情绪障碍,这是一种认识模式和解决路径;处理导致抑郁症的人生困难、挑战,这又是另一种认识模式和解决路径。
人生困难被医疗化这一问题在美国引发了诸多讨论,且治疗方式也发生了转向,然而在我国却很少有人提及。抑郁症被医疗化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概念建构与传播现象,它正在构建出越来越多的抑郁症患者,其带来的结果是把原本只是遭遇人生困难的人推向了病人的位置,促使大家都去服用药物。这个情况对个人而言不是好事,对家庭来说不是好事,对社会也不是好事。它可能会造就一个像马丁·塞利格曼所说的那样“抑郁、脆弱的社会”。
如果我们认同抑郁症是个体在遭遇关系冲突、伤害,面临人生挑战或者遭遇负性生活事件等困难时所产生的一种情绪反应,其表现为悲观、痛苦、消极、绝望(甚至出现自杀意念、自伤、尝试自杀的情况),那么,就不必那么紧张和害怕。人类始终在面对并处理这些问题。
是时候给抑郁症去除神秘色彩了,要还原它的真实本源和样子。从表面上看,数量众多的抑郁症患者所面临的问题,大部分都不是通过药物治疗能够解决的。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内塞指出“坏情绪有好理由”,并且人类的抑郁情绪具有进化的价值。这意味着,当人们遭遇人生的痛苦和挑战时,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痛苦和抑郁是正常的,它们是人生与人性的一部分。如果痛苦的强度过大或者太过激烈,那么当然需要进行治疗和帮助。然而,治疗并不仅仅意味着使用药物。范德考克指出,完全能够以非药物的途径来改变生理状态,进而达成内在(情绪)的均衡。
所谓非药物的方式,主要是心理咨询,或者谈话疗法。
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享有“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的盛誉,他是一位心理咨询大师。他一语道破了心理障碍的本质,指出心理问题和情绪障碍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关系和沟通不好所导致的。好的关系以及好的沟通(包含人际沟通和自我沟通)就像是解药。他进而认为,任何人,不仅仅是心理咨询师,只要学会用同情、理解的方式去倾听和接纳,就是在提供心理支持。
每个人都能够为子女、伴侣以及周围的人成为这样的人而提供支持和疗愈。当了解到抑郁症的真正诱因主要是父母、师长对子女、学生、下属的不良对待后,缓解和治愈抑郁症的路径就变得清晰了。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着手。
这种改变很迫切。
第二,当遭遇人生困难时,个人,特别是成人,并非仅仅会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脑神经科学已经证实,个人对于自身的情绪是能够进行主导控制的,而不是只能任由外部环境和事件来控制。这也正是如今在西方被证实并且广泛应用的 CBT(认知行为疗法)的科学依据和理念基础。CBT 的基本观念在于,外部的环境和事件并非必定会引发相同的感受与情绪反应。个人的感受和情绪反应和自身的信念、认知存在关联。个人始终能够对信念进行检讨,并且改变认知,借此摆脱情绪上的痛苦,走出抑郁的状态。
这并不意味着不改变触发情绪反应的外部环境,也不意味着不应对困难本身。就像意义疗法的创始人、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所说,这既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也是同时要做的事情。
首先,在一个社会中,若能做到平等、公正,贫富差距不会过于悬殊,竞争也不会过于激烈。这样的社会里,痛苦、焦虑、抑郁的人会相对更少。从这方面来讲,降低一个社会的抑郁程度以及减少抑郁者的数量,是全社会都应该承担的责任,需要全体人员共同去努力。
本文来自作者[qulangwang]投稿,不代表趣浪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qulangwang.cn/life/202504-15666.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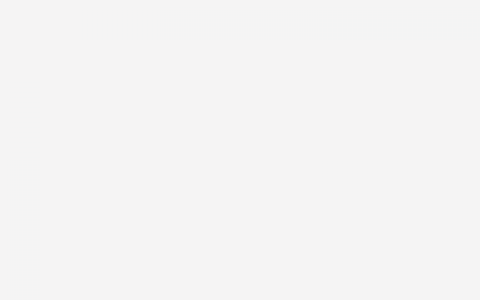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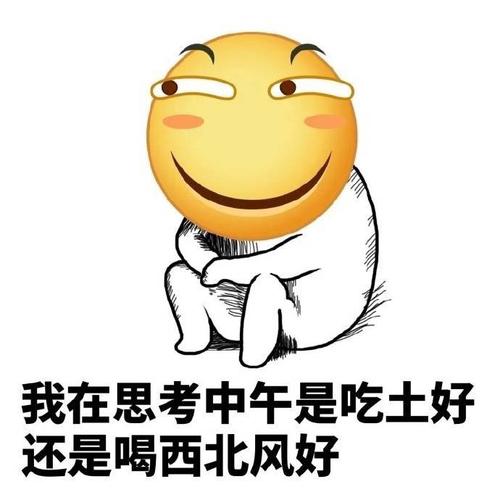
评论列表(4条)
我是趣浪号的签约作者“qulangwang”!
希望本篇文章《中国抑郁症患者数量激增:9500万患者背后的社会认知与青少年抑郁问题》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站[趣浪号]内容主要涵盖:生活百科,小常识,生活小窍门,知识分享
本文概览:从诊断、致病原因到治疗,抑郁症的生理-精神医学模式并不可靠,已经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