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语言与哲学
常有人说,哲学是难懂的,哲学是抽象的。也有人建议,哲学应该以更通俗的方式来撰写,之所以写得那么难懂,是因为自己没有弄懂。如果真正通透了,写出来的就会明白晓畅,比如看大师的文章,都是明白晓畅的。与上述意见相反,有论者认为,要讨论学术问题,就必须使用学术语言,难道能够不用电磁学的术语讲清楚电磁学吗?外行自然是读不懂的。你主张使用大白话,只是因为习惯了文化快餐。当阅读需要动脑筋时,你就责怪作者晦涩难懂。大师的文字又何尝容易理解呢?你去读读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他们有哪个是容易懂的?
报纸杂志上多次对这类问题进行过讨论。我自己也参加了一次这样的讨论。然而,哲学以及一般所说的学术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文风方面的问题,其背后还存在一些需要考虑的学理方面的问题。我今天尝试来谈谈这些学理问题。
日常语言也被称作自然语言。然而,“自然语言”与“日常语言”这两种说法的趋向存在差异。日常语言一般会与诗的语言、科学语言、咬文嚼字等进行对比,而自然语言主要是与人工语言相对应。实际上,正是因为提出了逻辑语言的设想,才出现了“自然语言”这一说法。
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了一次重要的变化,通常被称为语言转向。这种语言转向的范围很广泛,在分析哲学这一领域存在,在现象学—存在哲学—诠释学这一领域也存在。因此,有人认为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就是语言哲学。我们在此仅探讨分析哲学这一领域的语言哲学。
在分析哲学这一支的语言哲学内部,一开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去建构逻辑语言,另一种倾向是贴近自然语言。例如,罗素非常推崇逻辑语言,而摩尔则更推崇日常语言分析。尽管一开始就有这两种倾向,但粗略地来看,逻辑语言派在一开始占据着主导地位。像弗雷格、罗素以及卡尔纳普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都推崇逻辑语言。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应被归入逻辑语言学派。维特根斯坦很早就认为日常语言具备完好的逻辑秩序,并且他主张这种秩序需要通过分析来予以表明。他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所关注的是语言经过充分分析之后所得到的逻辑结构。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觉得,哲学在原则层面应当停留在我们日常进行思考的那些事情上。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杜威曾表达出相近的观点,即哲学思考的是我们的问题,而非哲学家的问题。
我们日常思考的事情,是用日常语言来进行表述的。如果耽留在日常思考的事情上,那就必须尊重日常语言的用法,也要尊重包含在日常语言中的道理。维特根斯坦指出,当我们从事哲学时会用到知识、知道、存在、对象、自我这些词,此时,我们必须不断地问自己:这个语词在日常语言里实际的用法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让语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方式回归到日常的使用方式。在此,我们能将“形而上学”大致理解为哲学理论。逻辑实证主义一直大力举起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帜,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逻辑实证主义自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而“我们”这些真正的哲学家,当下要去解构的,正是这种在现代较为流行的形而上学。
当然,维特根斯坦承认日常语言存在很多含混的地方,这会给更严谨的思考带来难题。不过,解决的办法并非去构建一套完全合乎逻辑的语言。有这样一段话经常被人引用:“我们步入了光滑的冰面,这里没有摩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条件是极佳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无法向前行进。我们需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还是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
维特根斯坦的这些思想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这个阶段形成的。差不多在相同的这个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直到五十年代,日常语言学派迎来了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他们都是英国的哲学家,并且都在牛津进行教学工作,所以,日常语言学派有时候也被称作牛津学派。实际上,牛津大学的其他一些学科也有日常语言分析的风气。比如当时在牛津大学担任法理学教授的哈特(Herbert Hart),他对日常语言分析的技术非常精通。1961 年出版的《法律的概念》这本书,被认为是法理学的经典之作。这一派哲学家中,有的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而有的则不是那么推崇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本人一直独往独来,一般也不把他归在哪个流派里。
维特根斯坦等人注重自然语言对于哲学的重要性,他们的著作通常以普通话写成,极少使用古怪且专门的术语。然而,我们阅读维特根斯坦等人的书时,依然觉得难以理解。虽然字面上几乎没有读不懂的地方,但还是无法像读故事那样顺畅地读下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我们平时以概念来进行思考,而哲学是针对概念本身展开思考。例如,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询问希庇阿斯:你能否给美下一个定义呢?请告知我什么是美。希庇阿斯回答说:一位年轻小姐是美的。然而,苏格拉底并不满意,他强调说,他所询问的是:什么是美?而非询问:谁是美的,什么东西是美的?在这篇对话中,希庇阿斯与苏格拉底尝试了多种关于美的定义。其中有美的就是适当的,美的就是有用的,美的就是令人愉悦的等。然而,苏格拉底对这些定义一一进行了驳难。最终得出的结论仅仅是:美是很难理解的。
照苏格拉底的意思,若要理解美的本质或理念,就不能仅仅知晓年轻小姐是美的,或者一匹母马是美的。我们必须去回答美本身究竟是什么,要能为美之为美给出一个定义。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学说,我们在此不予理会。我们只是想表明这样一种区别:我们平时会运用美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对美这个词做出恰当的定义。不只是美这类大词是如此。我们时常会用到“飞”这个词,也会用到“石头”这个词,还会用到“吝啬”这个词。现在我们停下一分钟,试着给“飞”下一个定义,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平常只要能够以概念进行思考就可以了,为何一定要去思考概念本身呢?不过,我们日常的思考有时候会让我们不得不对概念本身进行思考。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些争论。
张三说:我这么做,完全是出自对王五的爱,毫无自利之心。
李四不同意,并争论道:你看似是出于对王五的爱,但实际上你一直在背后谋划着自己的小算盘。
存在一种争论。同时还有另一种争论。李四或许会这样反驳张三:你对王五的爱属于你自身的一种利益,凭借对王五的爱去行事,这也是一种自利的表现。
我们思考一下,便能明白这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争论。我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
张三说:王五这么做完全是赌气,对他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李四表示不同意,他说王五赌气这样做了,他心里觉得痛快了,并且这也是对王五自己有好处的。
在第一类争论里,争论的内容是事实,即李四否认张三真的爱王五。在第二类争论中,李四不否认这一点,他所争论的是概念,也就是爱也是一种自私。此时,张三即便再努力去辩解他的确是出于爱而非自私,也是没有用的。如果张三要继续争论下去,那他只能向李四证明:爱不是自私的一种。
我们平常说话时,会将出于爱与出于自利分得很清楚。当听到“爱是一种自私”这样的话时,坚持常识态度的人通常会说:爱怎么会和自私是一回事呢?这分明是在诡辩。凡是与常识相冲突的,就是诡辩。不管我能否驳倒你,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依我们平常的感受,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动,然而哥白尼却提出地球绕太阳转。从常识角度来看,运动和静止是不同的情况,可赫拉克利特称一切都在运动,巴门尼德则说一切都静止不动。我面前的这张桌子明明静止得很安稳,可笛卡尔和牛顿却说它在运动,且在做匀速直线运动。生物学家道金斯创作了一本书,名为《自私的基因》。在这本书中提到,从基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具有自私性。比如妈妈对孩子的爱,舅舅舍命救助外甥,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为了获得遗传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早已运用了这样的思路:人的行为,无论是表面上被划分为自利的还是利他的,其根本上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这些说法与我们平常的说法差异很大,然而我们早已听惯了,并且差不多都相信了,甚至都意识不到它们与我们的日常说法存在冲突。
看来,我们坚持常识是有一定限度的。然而,这个限度究竟在何处呢?
第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我们在平常的经验中无法接触到,所以日常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汇来谈论它们。比如中子星、黑洞、基因、核糖核酸这些东西,常识无法触及到它们,它们不是日常语言所谈论的对象。非常粗略地来讲,日常语言主要谈论的是中等尺度的事物,而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则需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进行谈论。
第二种情况发生在建构理论的时候。我们通常说眼前的这个杯子是静止不动的,然而牛顿力学却将这种状态称作运动。这并非是牛顿喜欢闹别扭,而是这样规定运动这个概念有利于建构力学理论。为什么理论要对概念进行重新规定呢?这里面还有许多内容可以阐述,在此暂且不做讨论。
前面两种情况存在相互联系。大致来讲,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原本是借助科学理论才得以被了解的。若要将各种尺度的世界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谈论,日常语言或许就不太合适了,此时就需要采用不同的说话方式,也就是科学的说话方式。
还有第三种情况。我们通常在常识层面发表议论,用概念阐述事情而非谈论概念本身。然而,当遇到一些边缘情形时,仅仅谈论事实就不够清晰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做这件事是出于自利,做那件事是出于爱,这是很明白的。但是,妈妈为了孩子的利益,既损害了自己也损害了别人,此时她的爱是否是一种自利呢?推广开来,妈妈对子女的爱是否属于自利呢?母爱、对父母的爱、情爱、战友之爱以及对民族的爱,这些都被称作爱,然而它们似乎是不同类型的爱,它们与私欲、自利等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停下脚步,要把爱、自利这些概念本身弄清楚一些。谈论何种生活更快乐,何种人最幸福,往往免不了要对快乐、幸福这些概念本身进行一番梳理。
要弄清楚张三做这件事究竟是出于爱,还是借着爱的名义来满足他的私欲,主要牵涉到一些个别的事实,比如张三做这件事的诸多细节,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张三的一般人品以及张三一贯的行事方式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与其他人相比并没有权威。谈到爱和私欲这两个概念的分分合合时,哲学家应更敏感,也更善于梳理,因为这原本就是哲学家的本职工作。
但是每次提及此处,我都需添加一个注脚。梳理概念并非是一项从概念到概念的概念性游戏。要明晰爱和私欲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对爱和私欲拥有一定的经验,并且需要知晓一些涉及爱与私欲关系的事实,然而这些事实可以来源于任何地方,不一定是张三这一具体事例。
我们注意到,像“飞”这样的词,像“书”这样的词,它们的定义虽难,但用法清晰,我们几乎不会为它们的用法而争论。然而像“利益”“权力”“正义”“文化”“幸福”这样的词,属于论理概念,它们一方面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仿佛悬于日常生活之上,可说这些语词本身就带有理论的气息。实际上,这些概念时常会要求我们在争论过程中进行澄清。哲学家不会去梳理像飞、跑、书桌这类普通的语词,他们需要梳理的概念是诸如心灵、国家、正义、运动、美、命题等较为上层的概念。
这些被梳理过的概念,与我们日常语言的概念或许存在一些差别。主要差别在于,哲学着重语词的概念内容,重视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对于一个词的感情色彩、雅俗韵味等方面,通常不会纳入考虑范围。简单来讲,它们会变成一些边界更为清晰的概念,各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也更具逻辑性。维特根斯坦表示我们需时常提醒自身语词在自然语言里的用法,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哲学用语的意义就必须与自然语言中语词的意义完全等同。奥斯汀对此说得极为简明:日常语言是哲学思考的起始之处,但并非是思考的终点。
哲学家有时会取用一个专门的语词来区分经过梳理的概念,比如,平常我们讲“句子”,但在哲学著作中,我们常常不讲“句子”,而是讲“命题”。那命题和句子有怎样的不同呢?在德语中,我们所说的命题和句子都被称作 Satz。若两者存在不同,那便是“命题”仅针对一个句子的概念内容来提及这个句子,而不论这个句子的感情色彩等其他方面。
现在来看刚才引用的维特根斯坦和杜威的两句话。我们能注意到,他们既注重常识,也注重日常语言。然而,这并不是在表明哲学等于常识。哲学会思考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停留在我们日常思考的事情上”。但哲学并不等同于日常思考,要是哲学等于日常思考,那就直接叫它日常思考就好了,又何必叫它哲学呢?这里要讲的是,哲学会思考概念,然而它并非对哲学自身的概念进行思考,它所思考的恰恰是日常概念。需再次强调:哲学与常识的差异在于日常思考是以自然概念来展开的,而哲学是对自然概念进行思索。因为哲学所考察的概念是我们所拥有的概念,所以,即便哲学思考和日常思考不一样,但它思考的依然是我们的问题。
哲学用何种概念来对自然概念进行思考呢?可以表述为,运用哲学概念,运用逻辑性更为强烈的一套概念工具。然而,我必须即刻再次进行提醒,所谓的哲学概念,实际上不过是经过梳理后的自然概念。“哲学概念”这种说法很容易引发误解。好像哲学家拥有一套特定的哲学概念,如同电磁学家拥有一套术语一样。并且这些术语只要对电磁理论的构建有帮助,就可以不受到自然语词意义的限制。
归纳而言,我们在两个方向上能够接纳与常识相悖的说话方式。其一为建构理论,其二为梳理概念。此前我已提及,梳理概念是哲学的本职事务。而建构理论的工作属于科学家。现在我期望阐明的是,这两种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本质上存在差异,科学理论概念背离日常语言与哲学概念背离日常语言,在性质以及程度上均有所不同。
科学理论有其专属语汇,这是理论的一个标志。可以说,理论越成熟,其中的概念就离日常概念越远,该理论中的概念越依赖于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牛顿的运动概念与我们日常的运动概念不同,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责问牛顿。科学中的运动、静止、质量、弦等词与日常语言中这些词的意思不同,虚数这类词在日常语言中根本不存在。物理学家不必为此感到不安,也无需回到常识来为它们的用法进行辩护。物理学家认为,弦理论无法用常识的方式讲清楚,只有用数学公式才能讲清楚,我们不能因此就判定弦理论是个糊涂的理论。简单来说,这是因为科学家所处的是另一个世界。或者可以说,他们是以另一个层次来面对世界的。哥白尼提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并不意味着常识是错误的。在我们的认知中,太阳依然在转动,每晚依旧是斗转星移。出现错误的是托勒密的理论,而非常识。如果说常识出错,那是因为常识超出了自身的界限,将自身的结论当作了理论的结论。
哲学情况不同。哲学家的确会使用经过梳理的概念,这些概念或许与自然语言中的语词存在些许差异。不过,梳理只是将原本就蕴含在自然语言中的道理梳理得清晰明了,并非将某种东西强加给自然语词。倘若我们都认为是美的东西,而哲学家却说是丑的;我们都认为是爱的东西,而哲学家却说是自私的,那我们就应该怀疑是哲学家出现了错误。哲学家可以与常识进行争论,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说法。然而,在这场争论中,他必须向我们解释清楚他如此用词的缘由,并且这个缘由必须是已经蕴含在常识之内的道理。哲学语言并非全是日常语言,但它依然属于自然语言,而非技术性语言;就如同诗的语言并非全是日常语言,但它是自然语言,而非技术性语言。
我们从一个侧面的经验来观察上述的区分。读一本专门学科的书,若读不懂第一章,就难以读懂第二章,这是由于专门学科中的概念是经过特别定义的。而哲学书则不一样,可能有一段论证没读懂,但下一段论证却能够读懂。因为哲学论证大多是基于自然理解的,只是在某些地方对概念进行了一定的规定。
一方面,我们对哲学书难在何处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哲学并非一门特定的科学,在哲学书中,绝大部分都是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词。然而,这些语词是被用于探讨概念本身的,并非用于讲述故事。并且,这些概念时常会经过一些加工,它们与我们平常所使用的概念存在相通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哲学书里常提及“综合命题”,这里的“综合”与我们平常说的“综合”意思相近,并且有着更严格的逻辑限定。
这两件事,即概念梳理与建立科学理论,在古代是混为一体的。彼时,哲学等同于科学,科学也等同于哲学。或者可以这样说:在古代,哲学家们试图借助梳理概念来构建关于世界的理论。柏拉图期望通过探寻美的恰当定义来领会美之所以为美。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运动、变化、有限等概念的梳理构建了他的物理学。
近代以来,这两件事情逐渐分离开来。这个过程较为繁杂,在此不做赘述。仅说结果:科学家逐渐不再凭借梳理自然概念来构建理论。倘若我们的自然概念无法适用于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包括用仪器观察到的现象以及通过实验产生的现象,他们便会创造新概念,即创造科学理论概念,而不会费力去梳理已有的自然概念。
哲学家呢?他们依然在进行着概念梳理的工作。这样一来,哲学和科学就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从事哲学的人便会遭遇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再依靠概念梳理去构建关于世界的理论了,那么哲学究竟还有什么用途呢?
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维特根斯坦曾说过,哲学的作用具有治疗性质。这意味着什么呢?前面提到,在探讨快乐、幸福、正义、心灵等这些事情时,即便原本只是想要讨论某一个具体的做法是否正义,某一种具体的状态是否快乐,也往往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般的正义观念以及一般的快乐观念。我们平常习惯于就事论事,偶尔涉及一般观念时容易出错,比如从少数例子做出不适当的过度概括。只有在这种时候哲学才会发生,也就是说,哲学的作用是批判那些错误的定义和概括。所以,哲学具有治疗功能。
哲学治疗说时常遭到批评,且被指过于消极。此批评似乎并非十分恰当。医生的职责在于治疗疾病,而非使人长生不老,但这并不意味着医生的工作是消极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是否足够充分,确实值得进一步探讨。接下来我想借助一个例子来表明,观念治疗看似不只是一项消极的工作。
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赖尔通过概念分析来治疗某些观念错误,他的工作很突出。他写了一本名为《心的概念》的书,在书中,他运用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批判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笛卡尔将物体用广延来定义,将心灵用思维来定义。物质不具备思维能力,物体处于空间之中,遵循空间—机械的规律,可被公众观察。心灵没有广延,其活动处于内在状态。只有心的主人能够对其进行把握。这种身心二元论会引发诸多理论上的困难。在此仅提及一点,由于心灵活动完全是内在的,所以人仅仅能够知晓自己的心,无法知晓他人的心灵中存在着什么,而只能进行猜测。这便是近代哲学中著名的他人的心的问题,也就是他心问题。
《心的概念》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揭示语词的错误用法会致使心物二元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困难。这里出现的语词用法错误主要为范畴错误。例如:到华东师大进行参观的人问道,我看到了图书馆,看到了教室和办公楼,可华东师大究竟在哪里呢?另一个例子为潮水在不断上涨以及希望在不断上涨,这两个句子均是合理的句子。然而,倘若因为此就认定希望如同潮水一样是一种物质存在,那就犯了范畴方面的错误。两个词语或者语句的表层语法或许是相同的,但它们的深层语法实则不同。物体所处的位置以及心灵所处的位置从表面上看是同构的,不过前一种提法是有意义的,而后一种则没有意义。如果不能分清“物理过程”和“心理过程”属于不同的逻辑范畴,那么就有可能引发哲学上的混乱。
赖尔向我们表明,《心的概念》并非给予关于心的新的知识,而是对已有的知识的逻辑地图进行修正,把有关心灵的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给澄清。从这一意义来讲,我们能够说,对于心这个概念的概念分析给予了心的理论。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人们选取了错误的逻辑范畴去谈论心灵。笛卡尔的心灵学说在哲学家中是一种流行的权威学说,在普通人那里也很盛行。难道我们日常对心理语词的使用都错了,非得等赖尔来告知我们正确的用法吗?按照日常语言学派的普遍看法,错的并非我们日常对心理语词的使用,而是在对这些语词进行某些理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我们平常很清楚如何运用愚蠢、自信、有意和无意这些方面的概念,对于心灵和智力,我们也知晓很多很多。然而,能够利用这些概念进行论述,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论述这些概念,就如同深刻了解一个地方的地形却无法看懂那个地方的地图一样。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别,许多哲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谈论。比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到,土人对自己的河流极为熟悉,然而他们却无法画出一个河流航道的示意图。
矫正关于心灵的范畴错误,主要要看到,心理描述并非是对隐藏在物理现象背后的幽灵进行推论,而是在描述人的某些特殊种类的公开行为。赖尔得出结论:外在的各种智力行为不是研究心灵活动的线索,它们就是心的活动。当我们说一个人具有坚强的意志时,不是透视了他的某种微妙的心理活动,而是从他的行为举止中得知的。心智活动并非是脱离物理活动而存在的另一套活动,也不是一种隐藏在内的活动。心智活动是外在现象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且通常更为微妙的组织方式。丑角模仿笨拙人的动作,仅仅给你看一张照片的话,你是无法分辨他到底是真的笨拙还是在进行模仿。丑角做出的动作很笨拙,然而我们却夸赞他聪明伶俐。他与笨人的差别并非在于他头脑里的过程,也不是在于他头脑中的表演,而是在于他能够在各种场合进行笨拙的表演。我们所赞赏的不是第二套幽灵般的活动,而是他在我们眼前展现出来的技能。有意模仿笨拙既是一种心理过程,也是一种躯体过程,但并非是两个独立的过程。
今天我们对日常语言和哲学的一些学理问题进行了讨论。面对众多背景不同的听众,很多论题只是被提及了一下,并未充分展开。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等社科处下次让我来进行讲演时,我还能有一些内容可以讲。
本文于 2002 年在华东师大进行了一次讲演,该讲演稿之后在 2004 年 2 月 1 日的《文汇报》上发表。
本文来自作者[qulangwang]投稿,不代表趣浪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qulangwang.cn/life/202504-1532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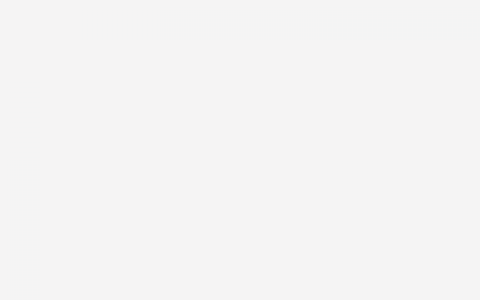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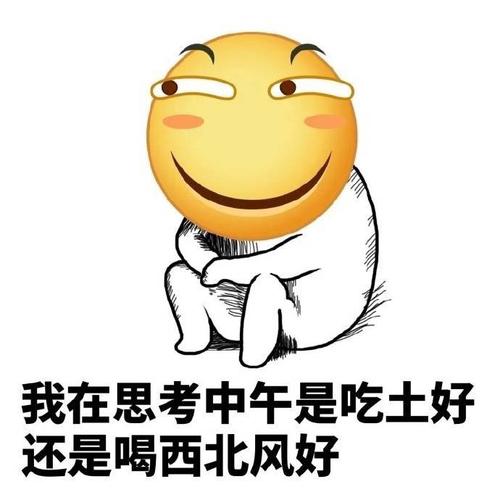
评论列表(4条)
我是趣浪号的签约作者“qulangwang”!
希望本篇文章《哲学与日常语言的关系:哲学难懂是文风问题吗?》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站[趣浪号]内容主要涵盖:生活百科,小常识,生活小窍门,知识分享
本文概览:日常语言与哲学 常听人说,哲学难懂,哲学抽象。也听人建议,哲学应该写得通俗一点,写得那么难懂,是因为你自己没弄懂,真正通透了,写出来的就明白晓畅,你看大师的文章...